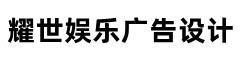全文阅读:罗伯特・弗兰克和沃克·埃文斯毫无疑问,任何人都能按下快门,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指。但说到眼睛,则完全不同。弗兰克的技巧充斥着他的个人特色:敏捷、大胆、笃定、极其不拘小节,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不符合所有的摄影技法。他就像一位浑然天成的大师,欣赏他的作品是一种愉悦。我可以将他的风格比作一种专业行为。如果手握一把锤子,那他完全可以快速精准地敲几下,就将钉子钉上。但如果不是很细心,虽然木板也会被钉牢,但木板上一定会留下锤子的痕迹。
1975年4月14日,罗伯特·弗兰克在韦尔斯利学院花了一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们中有十分之一的人都参加了一场为期一个月的“人文摄影”讨论会。弗兰克坦诚地谈到他不习惯静态影像的手法,以及对电影的诗意有着强烈的兴趣。就像之前的很多次,他试图解释十六年前自己为什么决定放弃摄影而投身电影事业。他还借此机会向观众们袒露,自己并不欣赏与会其他摄影师,如琼恩·米利(Gjon Mili),欧文·潘恩( Irving Penn),W.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在弗兰克的眼中,只有他的朋友兼导师沃克·埃文斯的摄影作品才值得深入讨论。埃文斯在弗兰克访问校园的四天前刚刚离世,他在这位比自己年轻的艺术家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我当时事业刚起步,(埃文斯)帮了我不少。他帮我拿到古根海姆的赞助。他话不多,但什么都懂。你们知道的,就像那种人,你不必说太多,但你知道他们能懂或他们能懂你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这方面特别惺惺相惜。
有时候事情就是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当我周游这个国家时,是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整体风貌。那时整个状态很好,我也受到了积极地影响。我了解沃克的摄影,非常清楚什么是我不喜欢的。
直到今天,史学家们也无法确定弗兰克和埃文斯到底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相遇。他们有无数的共同好友:路易斯·弗勒,郝伯特·玛特,本·舒尔茨和丹·韦纳。而且在1950年,他们有很多机会通过MoMA的摄影部总监爱德华·史泰钦相识。史泰钦在1951年MoMA的夏季展览“摄影中的抽象”(Abstraction in Photography)中展出了两位的摄影作品,所以如果他俩之前不认识的话,很有可能在史泰钦的介绍下相识。然而,最近弗兰克却宣称他们是通过灯具设计师兼油画家杰森·哈维(Jason Harvey)认识彼此的,当时杰森的父母就住在埃文斯在纽约上东区住所的顶层。从新获的这个信息中我们可以确定弗兰克和埃文斯是在1950年年初相识的。
从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来看,两位艺术家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弗兰克,一个外国人,身处异乡的苏黎世人,犹太人;埃文斯,美国中西部人,是生在圣路易斯市,长在芝加哥,还曾在安多佛中学和威廉姆斯学院等专属私立学校就读过的欧裔新教徒。几乎比弗兰克大两轮,埃文斯是个文气、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当时在为商人和广告大亨们提供服务的全国最高级月刊杂志《财富》当编辑。两人都是内向爱读书的人,但弗兰克更是个爱旅游的浪漫主义者,他蔑视权威,和自己的妻子玛丽在格林威治村租房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直到1936年,埃文斯放弃了他的市区身份,转而在东九十二街上买了一套公寓过起了小资生活。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开始结识一些权贵,也很享受离家很近的世纪协会(Century Association)那些精英会员同伴们单纯的陪伴。这个会员身份很快也让弗兰克受益。当埃文斯在1954年2月加入这个男性专属的俱乐部时,其中一个推荐人是亨利·艾伦·门罗(Henry Allen Moe),他是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秘书长(John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即使从一项对埃文斯事业的初步调查中也看得出:作为一位摄影师,他更偏向用大画幅相机,也就是说主体不动,在艺术家和他的被摄物体之间形成一种冷静情感的关系。而弗兰克则完全不同:追随直觉,有工作激情,使用小型相机,并且偏爱突发性碎片化的视觉结构。
弗兰克追寻无序性,试图避开控制感。相比传统图片的结构平衡,他更倾向动感的照片结构;相比纪录片式,他更倾向情感式的记录。如果说埃文斯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推崇与被摄物体之间产生心理上的疏离和审慎的距离;那么弗兰克就是位现实主义者,他的被摄物常常就近在咫尺。然而弗兰克和埃文斯都发现了能让彼此互相仰慕的闪光点,这种东西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而言是强大的,而且相当重要,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长久的友谊,这段友谊带给他们艺术创作的灵感。到了1954年晚些时候,弗兰克和埃文斯变成了工作伙伴和相互信任的朋友。不久埃文斯就以“博士”称呼弗兰克,而弗兰克也亲切地称埃文斯为“我亲爱的教授”。
弗兰克发现埃文斯是位对自己所选媒介非常着迷的艺术家,不仅在摄影作品的视觉结构上有着自己特殊的顺序,而且在保存私人文件、记录个人事务和友谊方面也有着独特的处理方式。
埃文斯是个典型的收藏家,今天的研究者们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沃克·埃文斯档案馆中发现了现存的专属他个人的手稿,这些可以用以解读他与弗兰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接下来,便是对两位极具创造性的艺术家之间关系进行更深一层的细致考量,这种考量并未停留在他们的摄影作品层面,而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对两位艺术家在1954到1958年这5年间的生活按时间顺序进行深入地研究,研究人员更详尽地审视了这段充满回报、发现、悲伤和真相的高品质友谊。
故事开始于1935年春天,弗兰克去美国的12年前,埃文斯就开始了一段长达两年的美国南部自驾之旅,他拍摄的那组照片取得了20世纪艺术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成就。弗兰克并没有看过埃文斯于1938年在MoMA里的标志性展览“美国影像”(American Photographs),但他非常了解随展发行的同名刊物。《美国影像》是一本在特定场所和遗迹上观察美国社会的写真,它表达了这个国家的欲望、绝望、以及传统形象。这本书以展现个人和文化群体为开端:棉农、阿巴拉契亚矿工、战争老兵、理发店、周末摩托车比赛、广告牌等;以对工厂小镇、乡间教堂、和木房子的研究为结束。
正是当弗兰克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之后的一切都已注定。可以确定的是,弗兰克在1955-1956年间,参与古根海姆基金会项目,在美国旅行期间身边一直带着这本书。
1954年1月31日,MoMA通知国际各大媒体,为了庆祝1955年博物馆成立25周年,将由史泰钦策划一场题为《人类一家》的大型国际摄影展。据媒体透露,史泰钦找寻的摄影作品类型是:“比起社会意识,我们更关心基本的人类意识……我确信,爱应该是《人类一家》这个展览的主旨和关键元素,因为它存在于每一个独立的小家庭中。”
史泰钦的这种宏大而民粹主义的主题激怒了一大批摄影师,其中就包括埃文斯,他谴责展览以爱和大同之美为主题,过度煽情和故作矫情。他拒绝参展,而弗兰克却提交了几幅作品,其中几张入选展览并出现在其联合出版物上。这里面也包括了两幅玛丽·弗兰克的作品,她当时还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安德里亚。孩子出生于1954年4月21日,在投稿截止时间后不到两周。
在夏初的时候,埃文斯与简的第一段婚姻陷入了危机,为了摆脱折磨,他独自一人去伦敦和巴黎进行了一场豪华旅游。在离开的那段时间,简和《纽约客》的音乐评论家温托·萨吉安(Winthrop Sargeant)展开恋情,当埃文斯从欧洲回去后,对于简不忠的事情,他似乎既觉得解脱又觉得不可置信。尽管他们直到1955年晚秋才真正分居和离婚,但在这之前,埃文斯已经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上都准备好了发展新的关系。受益者之一就是弗兰克。埃文斯鼓励他向古根海姆基金会递交申请,同时也同意提供一封推荐信。10月21日,基金会收到弗兰克的申请,想为他拍摄美国的项目找份资助。两天后,由于埃文斯答应在紧接着的一月为他写封正式的推荐信,弗兰克写了封诚挚的感谢信:
亲爱的沃克,不好意思,又打扰您。我只是想谢谢您!你的善意是我生命中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向简问好!
然而,保存下来的文件显示埃文斯对他同事的帮助远不止于此:他是弗兰克古根海姆申请信的主笔。埃文斯巧妙地重写了弗兰克的一页临时打字稿(注解出自埃文斯之手),将它扩展为长达四页的手稿。之后,弗兰克将其打印出,并作为古根海姆项目申请上交。
对弗兰克草稿和埃文斯重写版的详细分析显示,最终版并不完全出自埃文斯之手,因为还能看到纸上弗兰克原来的框架。许多申请者常用的主题,如将摄影师作为档案保管员的描述和将其照片分类到各个领域这样的语句,完全没有出现在弗兰克对原文的构思里。
埃文斯又对弗兰克申请项目的可用之地和方法加注评论:“我的整个项目会有大量作品产出,就像摄影师们使用小型相机拍摄一样。随着项目的发展,我想在拍摄现场就将作品分类做标注。最终形成的文件可像议会图书馆的文件一样,收录成集。目前可想到最直接的用处,就是出版成书籍和杂志。”埃文斯用突出的专业名词强化了这篇申请,如:纪录片、视觉影响、视觉、美国、观察和记录、文明、目录等。
作为好朋友和支持者,埃文斯将自己对摄影师角色的理解付诸于弗兰克身上,将弗兰克重新包装并意图打动基金会的评委们。作为古根海姆的前成员,埃文斯做了多年基金会咨询委员会会员,他对弗兰克的支持取得了加倍成效,不仅是因为重写了弗兰克的申请信,为他亲自写推荐信,更是在必要时,为基金会奖金项目投了同意票。
那年是以弗兰克答应埃文斯为《财富》制作一个小型摄影作品集,和期待着古根海姆基金会资助旅行项目而结束的。在1954年12月或1955年1月初制定的摄影项目是一项斥巨资的冬季手作:拍摄那些乘坐从纽约到华盛顿特区“国会号”快速列车的商人和政要们。尽管弗兰克和埃文斯在其他项目上也有过合作和互助,但这是唯一一次两位艺术家作为摄影师和编辑合作。这个项目最后以名为“休闲车厢,在路上,从纽约到华盛顿”(En route from New York to Washington, Club Car)的照片集收录在《美国人》最早的一批照片中。
而埃文斯的1954年却以悲伤结束。当时他非常确定自己的婚姻已注定走向尽头。而12月的时候,自己最信赖的朋友及长期合作伙伴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开始受心绞痛的折磨,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五个月后,艾吉在去就医的出租车上逝世。
1955年1月24日,MoMA 在备受瞩目中展出了《人类一家》。尽管史泰钦在展览和同名书中隆重介绍了弗兰克的摄影作品,但弗兰克后来承认在展览期间,博物馆并未展示出他对摄影的真正兴趣点。“史泰钦非常欣赏我,对我也很好。我非常认同他对摄影的情怀。当时我用尽了美丽的个体意象。我清楚我活在不同的世界中,那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拥有湛蓝天空,所有照片都完美无瑕的神话。”然而,在MoMA的展出摄影作品并未影响古根海姆基金委员会对弗兰克申请项目的评定。
在《人类一家》面向大众展出的两周后,为了支持弗兰克,埃文斯向古根海姆基金会递交了一篇行文讲究、言辞有力的推荐信。
我认为,无论如何,这个年轻人大概都是现如今年轻摄影师中最有才华的。我非常了解他的作品,同时也很了解他的为人,所以即使他并未申请会员,我也愿意举荐他。如果真是那回事的话,那罗伯特·弗兰克定是位天生的摄影师。说他是位天生的艺术家,因为他天生的观察力中还加入了后天的思想、练习和学习使用小型相机。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他俨然成长为一位极其严谨且具有深邃思想的工作者。想象力,是我觉得他最突出的天赋,这是上天赐予他的敏感天赋,或者说是诅咒。从事摄影行业的人里极少能如此面面俱到。我见过的一些照片都是由其他领域的一些有如此天赋的人拍摄的,如福克纳和斯坦伯格拍的那些有名的快照。然而,萧在拍摄时的视觉感却并不敏锐。我认为罗伯特·弗兰克在摄影领域正火力全开,所以我非常希望看见他得到鼓励。
能想到代表弗兰克优势的两个例子是:几年前,他在威尔士煤矿小镇卡劳拍摄的一组照片,讲述了那儿的一位煤矿工人的生活。还有最近,受我之托在《财富》当记者,报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上的国会专属列车。这两个项目,一个完全出于自由意志,一个是商业化摄影,都极具创造性、全面性和智性。这让我想到,毕竟,智慧也是天赐异禀,而我应该声明弗兰克是具备的。在信里,我好像毫无保留地赞美了弗兰克,这也不太对,因为毕竟他也会犯错。他曾尝试拍摄一个城市街区,但我认为照片的质量却未得到保证。但威尔士矿工系列却流露出诗意;且在国会专属的任务中,他展现出了一位摄影师具备的且应具备的足智多谋。
说到弗兰克申请的这个项目,我相信在美国之旅中,他能够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我认为他已在这个计划中向您展示了他为自己划定的范围。如何选题将比较困难,但他有能力处理好。
写完推荐信后,埃文斯雇佣弗兰克为技术助手,开始为《财富》2月早期的一组新的摄影集工作,这是一组描绘日常手工工具的照片。这个项目于1955年7月以“日常工具之美”(”Beauties of the Common Tool”)的名字发表,是埃文斯为该杂志工作20年中画面最生动、表达最抒情的一个项目。
埃文斯是否真的需要弗兰克的技术,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都很享受这个项目的合作。他俩徘徊在第二大道的五金店里,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看似有趣的工具搜寻,如:开箱器、铁皮剪、钳子、转动扳手等。然后,他们把宝贝们带回埃文斯的工作室,拍摄这一系列有着最小影子的物件。杂志付给弗兰克45美元,作为他在这个项目上贡献的回报,可这笔数目远不足以抵付他俩买那批工具花的71.27美元。
然而,弗兰克微薄的收入马上就会得到改观。5月1日,雅各布·德钦(Jacob Deschin)在《纽约时报》上宣布只有两位摄影师被授予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创作奖金,分别是:弗兰克和托德·韦伯(Todd Webb)。尽管迫不及待想开始他的项目,但弗兰克还是在5月16日艾吉去世时留在了纽约。这位离世的作家年仅45岁,身后留下了他的遗孀米娅,两位前妻,三个孩子和埃文斯生活中巨大的空虚。埃文斯因好友离世产生的沉痛同时也影响了弗兰克:
艾吉去世时,我去他在《财富》的办公室看望他……我记得他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前,从窗户向下看可以看到洛克菲勒中心,你知道的,就是他们滑冰的地方?他就呆呆坐在那儿,哭了……我想说我被……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见过他在一些特定情境下的样子;我和他一起去新英格兰拍摄磨坊……然后他妻子离开了他,那时他非常难过……他要上课,你知道的……我很震撼……我是说他非常智慧……但却不外露……尽管我确信他拥有聪明才智……但他从不用它们。
弗兰克提到的“拍摄磨坊的旅行”(“trip to photograph mills”)可以被追溯到5月至7月末间,这次他作为埃文斯付薪的助手,是为《财富》做的第二个项目。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埃文斯其实并不那么需要一位助手,让其作为他的旅伴让他开心或者为他驾驶那辆拉风的敞篷别克路霸。一张弗兰克在车上看似等着埃文斯完成他拍摄工作的35毫米柯达铬黄快照证实了弗兰克再三发表的评论,埃文斯其实并不鼓励他的朋友真正参与到图片制作的过程中。
直到十二月末,除了一些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为《财富》开展的工作旅途外,埃文斯没有再做任何的日记记录,他在1955年夏和秋的日常活动也鲜有人知。但7月末,在《财富》刊登了工具合集的期刊后,简·埃文斯永远地搬出了他们的公寓,他们将在那年年末离婚。
1955年秋天,弗兰克驾驶着一辆福特1950离开纽约,开始了他古根海姆项目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他驶向迈阿密,然后经过亚特兰大向西到孟菲斯,又向南去了新奥尔良。弗兰克基本上是轻装上阵。除过相机,胶卷和一些换洗的衣服外,他只带了两本美国旅游指南:美国汽车协会的一本记载高速路、城市和乡镇习俗的公路地图集和埃文斯的著作《美国影像》,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地图。两本书好像都被埃文斯标注了推荐路线和值得专门绕路去看的地点。
关于弗兰克的采访暗示出,在这次神圣的公路之旅途中,能够催化他进行拍摄的其中一个强烈的情感驱动,就是他被囚禁在阿肯色州的市监狱里,并回答了一系列炮轰式问题的漫长的一天。就在1955年11月7日午后刚过,阿肯色州立警察在并没有出具任何文件说明的情况下,在路上拦截了弗兰克,原因可能只是他开着一辆挂着纽约牌照的最新款汽车。警官们对他的车进行了搜查并在附近的监狱审讯了弗兰克,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他都被拘留在那。
警察指控弗兰克是一名者,并让他解释“布尔多维奇”,这个听起来像俄国名字并出现在古根海姆创作奖金一系列参考文献上的男人是谁。他们质问他为什么且如何能在底特律守卫极严的福特迪尔伯恩胭脂河工厂进行拍摄,为什么他能访问阿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因为那儿从193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种族动乱地带。(弗兰克否认知晓“斯科茨伯勒男孩”那个臭名昭著的案件:九名非裔美国青少年被指控强奸了两名白人女性。)他甚至还被要求解释为什么身为犹太人,他要在战后返回欧洲。更有甚者,一位特别警局调查员还威胁说要把弗兰克所有的胶卷都冲印出来,其实是想借机在镇上弄丢它们。
弗兰克选择向埃文斯倾吐痛苦并寻求建议明证了两人坚固的友谊。收到弗兰克的求助后没几日,埃文斯就将原信发给了弗兰克的律师。律师应该是启动了一系列程序,试图检索和消除他的客户在州警局文件上留下的指纹。弗兰克担心这会断送了他申请美国公民的正常流程,正如他在信中写的,他的手印备案在警局让(正常流程)变得“不可能”。奇怪的是,沃克·埃文斯档案馆里保留了比早前公布内容多一页的弗兰克原稿信件。被埃文斯保存的这张纸的边缘有他抄写的弗兰克的信件内容,是在把原稿交给弗兰克的律师之前,他誊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真是令人震惊。
我签了一个声明,所以我所有的物品才能完好无损地归还给我。我之前注意到那个副职影印了我的护照并悄悄装进了他的口袋,我当时要求签署的声明里也应该提到这张,他就火了,我觉得是在那之后他就决定要采集我的指纹。我在两份不同的表格上按了手印,每一张按了两次——其中一张表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常规表格。我还得在两张上都签字,我拒绝了,但被告知,如果不签就得重返牢房。我在牢房的情况和审讯我的人的情况,之后再跟你细说。这是给未来拍部电影提供的好素材,但当时我可没法想到这点。【我不得不在标题:罪犯的下面签名】
弗兰克在阿肯萨斯州被捕的第三周后,也就是11月26日,他又致信埃文斯。玛丽·弗兰克和他们的孩子们飞去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与弗兰克汇合,所以现在他的行程成了举家旅行,精气神更好了。弗兰克深知,作为一名资深美国公路文物收集者,埃文斯肯定会喜欢这个印着公路地图、高速路标、标语(“世界羊毛及马海毛之都”)、当地地标广告的海沫绿色酒店文具。弗兰克本人很欣赏这种大胆的尝试,并且在其之上加入了自己的图标。
从圣达菲往西驶向拉斯维加斯的途中,弗兰克将会在报纸上读到或在汽车广播里听到发生于12月1日的罗莎·帕克斯和抵制蒙哥马利公车事件。当他开始横跨全国的公路旅行时,他也许对美国经历并不具备一个特别完整清晰的政治观点,但路上所发生的那些情况完全可以帮他形成。他和帕克斯现在都被州政府定为“罪犯”的经历,一定唤起了他童年的记忆:作为一个无国可归的犹太儿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年流亡瑞士。
回到纽约,埃文斯的个人事务和在《财富》的工作占据着他年末的那段时间。他在为一个MoMA的新展做暗房工作。他12月的大部分时间和1956年1月早些时候都花在为史泰钦的四人展“手握相机的第欧根尼”选取和影印34张摄影作品。史泰钦邀请每位艺术家贡献一篇声明,如往常一样,埃文斯不懈地修饰和完善着出现在墙上和发表在出版物上的文字。人们阅读他的短文,是作为对那种他崇尚的、出自弗兰克之手的摄影工作的另一种形式的支持,也是作为对他体制内的赞助者的一种抨击:
(正当的)真正的摄影,像幽默笑话一样,看似是一件太严肃而不能被严肃讨论的事情。在一个注解中,如果它不是被最终定论所定义,那一定是没有权衡思考的结果。它不是杜勒斯国务卿从一架飞机中走出来的画面,它不是可爱的猫群、不是触地得分、不是裸体、不是母亲身份、也不是制造商产品的安排。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不会是任何靠近海滩那种地方的任何东西。简单来说,它不是谎言,不是老套的东西:别人的想法。它是融合了切身的体会后的原初景象,别无其他。
这年的一开始对埃文斯来说就是一个高潮,他开启了一个新项目——致敬艾吉。1940年艾吉为埃文斯的地铁肖像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但这篇文章和在那个摇晃的充满汗渍的盒子里拍的任何一张有创意且引人深思的照片都没有被发表。埃文斯在一个只短暂存在过的哈佛文学杂志——《剑桥评论》里为这个材料的呈现找了个一席之地,打算向哈佛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艾吉致敬。“艾吉”期刊发表在3月20日,其中包括一本未完的自传体小说《家中丧事》(A Death in the Family)里的一个已经编辑的片段,还有用高质量的珂罗印刷重新制作的8张埃文斯的地铁照片。
在埃文斯准备这些印刷品时,弗兰克正在洛杉矶和玛丽及家人苦苦挣扎,试图寻找付薪的杂志编辑工作,如:《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和《生活》,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断档期间,他写信给父母,讨论他慢慢改变的旅行态度和目标:“我不仅努力地去拍摄,更是想要在美国的照片中传递一种观点……这儿有很多我不喜欢且永远无法接受的东西。我试图将它们呈现在照片中。”
比起接杂志的活,弗兰克更需要申请将古根海姆创作奖金再延期一年,并且他又一次申请做了埃文斯的助手。2月27日,他给埃文斯寄去一封信,信中还附有一沓凌乱的笔记,玛丽对它们做了注释,将他在旅途中到目前为止取得的进步都标了出来。这封信显示,在弗兰克不在纽约的那段时间,他把埃文斯朋友及赞助人的身份提升至了“我亲爱的教授”,为两位艺术工作者之间亲密的友谊冠以荣誉名号。
我会在旧金山冲洗一些照片。如果能跟基金会续签的话(这期快用完了),那我会很愿意慢慢开车回纽约。这儿也许比起刚开始时,我现在对这个项目更感兴趣了。在洛杉矶生活的两个月就像在巴黎的一所医院住院——你会见到在巴黎所有恐怖的事情——在洛杉矶你能看到恐怖的美国被展现。如果你不得不待更长的时间,那事情很快便会更糟。昨天我帮本【舒尔茨】(自从我离开纽约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棕榈泉的车赛干了点活。请等我把在那拍的一些照片展示给你。(请别告诉本我还用黑白胶卷拍了同样的照片。)我确定知道我不会再尝试这种项目了——(对我而言)它就像一个你画完的圆【画小圆】,而且是你一笔画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我能完成它。今年。所以,亲爱的埃文斯教授——做您的作业:【完全划掉了】
如果埃文斯提交了另一封推荐信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话,那么他好像就不会保留这封信的复印件了。到了4月份,弗兰克收到了来自基金会的续签,他又给埃文斯寄了另一封诚挚的感谢信。玛丽也附上了她自己的感言条并加了段极其逗趣的描述:弗兰克剪了个新发型,发型的灵感貌似是从长期待在洛杉矶那群好莱坞作家和编辑们身上汲取的,而他们则让人不敢置信的富有。
来自于5月中旬的这封信证实了弗兰克拍摄“酒店窗外的风景——比尤特,蒙大拿”(View from hotel window---Butte, Montana)的精准定位,这是《美国人》里最富盛名的一张照片。透过单薄的窗帘向他在上层的房间窗外望去,弗兰克拍摄了一张挽歌式的、又似阴郁的照片,照片中满目疮痍、光秃秃浓烟四起的小山丘从死气沉沉的城市中突起——在信纸上被描述为“地上一公里,地下一公里,地球上最富有的山丘。”弗兰克并未在信中提到这个景观,但他却给埃文斯提供了一个迷人的纪念品,一个他在当地酒吧厕所发现的色情涂鸦。
路上度过了八个多月后,在1956年的6月的某个时候弗兰克回到了纽约,不久后又重新开始他的旅途。8月,他拍摄了于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大会,其中最后几张也被收录在《美国人》里。尽管埃文斯和弗兰克也许会经常电话联系,但这个夏天的多半时间他都在欧洲投身于《体育画报》的项目。大概是在10月,弗兰克从芝加哥回去后,他们才又见面。那个时候,弗兰克应该是有机会冲洗出一大批那年在路上拍摄的照片的。
两位男士在10月4日共用晚餐,于24日在埃文斯《财富》的办公室见面,又在第二晚一起吃晚饭。在三周的间隔里,弗兰克已经着手为那本最终成为《美国人》的书进行照片排版了。书的介绍是件不断困扰弗兰克的事。
10月8日,在见过埃文斯的四天后,弗兰克向兰登书屋的编辑萨克斯·康明斯(Saxe Commins)致信,询问是否可以将他的照片拿给威廉·福克纳看,想了解下作家是否愿意为未来的出版写篇序。这只是弗兰克的想法还是埃文斯给出了建议呢?第二个假设看似是可能的,因为埃文斯在为弗兰克向古根海姆基金会写推荐信时,引用了最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福克纳。无论是谁的意图,福克纳都拒绝了,或者说没有回应,所以这个谁将为《美国人》写介绍的问题被搁置了几个月。
编辑和冲印照片的任务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他们10月见面时,弗兰克有可能留给埃文斯一盒或两盒冲印照片,这些几乎瞬间勾起了雷·麦克兰(Ray Mackland)的往昔情感,他是《生活》杂志的高级图片编辑同时为MoMA 最有影响的五位摄影委员之一的。这无疑是埃文斯为另一位艺术家写的最仗义的注解。
我刚刚观赏了一组关于美国最丰富、最有原创性的照片,这让我沉浸其中。它是个专场秀——罗伯特·弗兰克的古根海姆项目刚刚竣工。之前由我经手了一组由弗兰克在《财富》拍摄的影集,效果甚佳;但他的新项目显然不是《财富》的风格,或者说,作为一本商业杂志,我们无法以正确的方式来断其优劣。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介意我向您推荐弗兰克的新作品。私认为这些照片是极可贵和成熟的作品。如您所知,弗兰克不是推销员(我也不是),但我认为不管怎样他都会来拜访您的。
希望我的来信没有太乱方寸,但澎湃的心潮促使我将这组照片划定为一个杰出的摄影项目。
虽然如此,弗兰克仍继续致力于古根海姆项目的照片,1956年秋和1957年春多半时间他都在冲印底片,并且为要出版的书设计草图框架。即使没有美国出版商对他的新书感兴趣,他也计划着可以寻求罗伯特·德尔皮尔(Robert Delpire)的帮助,在巴黎制成某种形式的出版物。弗兰克直接和这个法国出版商联系,他在1956年9月初出版过《印第安未逝》(Indiens pas morts),其中有弗兰克、沃纳·比肖夫和皮埃尔·费杰(PierreVerger)的摄影作品。
尽管健康状况多次出现问题,埃文斯仍在1957年和1958年保持着高活跃度和高产,他为《财富》的五个影集出版和撰写了一些照片和文章,并分别为《体育画报》和《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各完成了两个影集。那年春天,弗兰克也同样多产:他得知戴乐比尔(Delpire)将出版他的一大批照片。到夏天的时候,他将千张照片缩减到85张,从而完成了一本书的框架,同时在Les Américains(《美国人》法语版)和接下来的美国版《美国人》都敲定了基本样式和照片的排序。
从戴乐比尔那儿得到了保证,弗兰克就在1957年晚春的某天邀请埃文斯为法语版的书撰写介绍。保存在沃克·埃文斯档案馆里的手稿和打字稿都清楚地显示了埃文斯相当看重这个委托。这些文件显示他独到的眼光,他试图定义弗兰克照片极强的影响力:“摄影工作可以多么具有主观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特定的人手中会变得有多主观?苦涩的诙谐,尖酸的震惊;”“将艺术家称为发明家的情况不是太过度而是太少。”“要做一件没人做过的事,需要的远不止原创力。剩下的一些因素就包括,要将遗忘转化成好习惯。”
我要为罗伯特·弗兰克正名,他就是那个走遍美国南北拍下这些照片的人。若要呈现一个民族的面貌,真相本身就是矛盾的。摄影,那个机器记录者在一个本身就带有主观看法的人手里也会变得主观。我认为弗兰克的照片带有主观性,但这些也许对于了解图像语言和眼睛言语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弗兰克的照片也许对这些有发言权的人来说是无法转译的,他们会立即察觉到这个摄影师的智慧、他并不柔和的诗篇、他惊人的才智和他良好的道德感。至于对那些眼睛已经被媒体图片和所谓“美”的自满的复制品腐蚀了的人来说,这些特质也许会毫无疑问地被立即忽略掉,除非一本像这样的书,用一点出版了的【铅笔添加:视觉】觉悟能震撼到他们。
我得承认,在准备充分的弗兰克横穿这个国家时,无论上帝向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都一定是面带笑意的。多数摄影师是熟悉这个感觉的:是在他们为胶卷上发现的一些东西而惊讶的时候。确定的是,弗兰克不仅常常感到惊讶更是被毫无防备地震惊了。那些头戴丝帽的政治家们流露出的虚伪和自大,是那种极其经典的连基层政客都能表现出来的表情,他对着他们按下快门时是否是个偶然?或者他恰巧在加利福尼亚的某处看到滑稽的【插入:小丑式的】癫狂和滑稽混乱的胜利,是因为一个男人坐在他的花园里沐浴着该州众人皆知的阳光?无论是否是巧合,都让政客们和加利福尼亚园丁当心那些时刻吧。
但是这些例子并不是弗兰克视角的精髓,那是一个更积极更宏大的东西。观看他那些装着人物、路边风景、城市活力【插入:熔炉】、半神的孩子们的非理想主义照片激发了涟涟泪水和些许希望,而不是【插入:任意一个都太少】些许的嘲讽,如任何人将看到的【插入:你能看到的这个】他以那些回应美国。他向一个一般情况下没有笑话存在的国家展示了可笑;成年人对青少年或多或少的疏离,但他比……更值得【插入: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立场和腔调一个艺术家的。在这个【插入:他的】立场中,是【插入:是一位拥有……姿态】一位极其成熟、美好天赋、极深怜悯心的艺术家。
埃文斯和弗兰克都未公开谈论过此事,所以只能猜测要么是弗兰克要么是戴乐比尔(Delpire)毙掉了这篇文章。埃文斯好像也接受了这个拒绝,没过多久就同意为在《美国相机年鉴1958》发表在1957年12月早期的一本选集改编他的评论,并进行发表。年鉴以一个异于寻常的设计插入了弗兰克古根海姆项目的33张照片。埃文斯为戴乐比尔(Delpire)最初构思的文章被安排在照片之前;弗兰克的一个声明排在它们之后。
后来到秋天的时候,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的社长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和他的出版物长青类书籍出版了他新的文学杂志《长青评论》(Evergreen Review)的第四期。他们复制了“新堡,纽约”(Newburgh, New York)作为杂志封面,这是弗兰克古根海姆项目照片集里第一张发表在美国的照片。正值变化中的美国青年文化和主流书籍的出版,此图像(公路赛车会上的摩托车手)的选择和出现的时间不能更合适了。
1957年9月的第一周,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已经出版了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该书立即成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关于追寻传统美国社会之外成就感的经典小说。其中一版书的封面推荐该书为“让我们了解当下狂野的青年人和他们对体验和感受狂热追寻的一本引起热议的畅销书”。
弗兰克在1957年年初的某个时间,在《在路上》出版不久后与凯鲁亚克见面,他立刻向凯鲁亚克展示了或许是书的草图(被戴乐比尔(Delpire)归还)或许是一组古根海姆项目洗出来的照片。几周之内(也许是几天),凯鲁亚克就完成了最终印刷在美国版《美国人》中的短文的初稿,这个初稿同时取代了埃文斯的评论和戴乐比尔(Delpire)不久后将出版的《Les Américains》中大量混杂的引用。
尽管看起来像是弗兰克在他和凯鲁亚克第一次会面时就自顾自地邀请对方为他的书撰写一篇文章,但更有可能是发生在弗兰克阅读埃文斯为此书写的初稿之前,这更符合他的风格。到了10月1日,凯鲁亚克写了这篇短文并在一篇寄给在巴黎的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一封凌乱的信上做了评论。但不知为何,戴乐比尔(Delpire)拒绝了第二篇文章。
精神的联盟和理想的友谊已经开始转移,这将把弗兰克从他和埃文斯的联合和从传统摄影历史引向一个更现代、挽歌式的视角,从而助他获得在摄影上的成就。他应该了解埃文斯在《美国相机年鉴1958》中刊登的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乔治·桑塔亚纳的话并无特别目的,正如将他的照片直接和《Les Américains》中的文章联系起来也没什么好处一样。弗兰克真正想要的是一些实验性的、主观的、也许更无序和感官的东西,正如凯鲁亚克和金斯堡发表在罗塞特的《长青评论》上的文章一样。弗兰克和这些更当代的文学家们产生关联将只是时间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甚至是埃文斯本人也对从项目中抽离一些而感到满意(全心投入在他的得宠者身上),放任弗兰克飘往精神之所向。
经历了数月的暗房工作后,弗兰克重新拾起相机,并在1958年开始投身于他后来声明的最后一个摄影项目——从移动大巴的窗户看纽约的街景。同时他还说服那时还是个小期刊的《Pageant》杂志的编辑们,在一个风格独特的有深度的图片文章中刊登一系列古根海姆项目的照片。“一本《Pageant》影集:一个人的美国”(“A Pageant Portfolio: One Man’sU.S.A.”)在4月发表,其中的一些照片既没有出现在《Les Américains》中也没出现在《美国相机年鉴1958》里。
1958年5月15日,德尔格兄弟(Draeger Frères)印刷了《Les Américains》,收录在戴乐比尔(Delpire)的“重要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essentielle)选集的第五卷里。尽管照片题目是英文的,但包括来自美国的资源,所有的其他文章都是法语。对于一个摄影出版物来说,这个封面插图出人意料地对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由一些简单的钢笔画和方格纸组成的拼贴画进行了调整,那个拼贴画是在联合国总部成立时(1947-1953)做的。斯坦伯格的插图将出现在《Les Américains》的封面上,同时书中还伴有福克纳的文章,真是绝妙;这是因为在整个项目的最开始,极具艺术家气质的埃文斯提议需要将弗兰克的作品放置在一定情境中。而埃文斯的名字却在《Les Américains》里无处可寻。弗兰克或许在赠给埃文斯的那本书的空白扉页上的献词里,提到了这个令人叹息的事实:
1958年11月末,当第一批《Les Américains》的成书寄到纽约时,埃文斯正经受着溃疡之苦,需要在12月做两次手术。55岁时,他开始慢下来,感受生活。弗兰克和埃文斯在1958年的整个秋天都保持着联系,但如果埃文斯的日记是个可靠的风向标的话,两位艺术家从现在起已经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行进了。他们的关系已经成熟到了埃文斯需要寻求弗兰克的帮助和支持。
1959年4月7日,在埃文斯向在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亨利·艾伦·门罗递交资助申请的前一天,这是他自从1940年以来的第一份资助申请,他致电本·莎恩(Ben Shahn)和弗兰克,劳烦他们为自己写推荐信。他们同意了,就像杰森·艾普斯坦(JasonEpstein )罗伯特·贝弗利·黑尔(RobertBeverly Hale)海伦·莱维特( Helen Levitt)和爱德华·史泰钦当年的做法一样。埃文斯的日记条目显示他试图请莱维特和弗兰克撰写推荐信并以他的名义提交。
埃文斯向古根海姆基金会提交的项目是编辑一本全是新照片的书,书中将或多或少囊括当代历史:“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遗迹见证;恢复的迹象;战争或种族问题的迹象;像清教主义、理想主义、物质主义这样具有美国特征的迹象;动荡和孤立的见证,庸俗的所在;文化和世俗的见证……意在表达有深度的准确性,反应当代真理与现实;小事中偶然的严肃性和与之相对的大事中的无趣。总而言之,埃文斯构思的东西尽管从来没有试图完成,但他还是赢得了赞助。这是一本类似弗兰克古根海姆照片的杰出专著《美国人》的书,由凯鲁亚克作序,格罗夫出版社将要在1959年晚秋出版的。
多年后,在1971年的夏天,埃文斯做客弗兰克在新斯科舍省马布的家。刚从另一轮腹部手术中康复一点,也才和他第二任妻子分开,埃文斯独自旅行并与弗兰克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琼·丽芙待了一周。和弗兰克一样,埃文斯也被面朝大海的粗旷风景所吸引,他拍摄了通向海洋的斜坡,还有引向弗兰克木屋和周边其他建筑的小路。
然而大部分照片记录的都是弗兰克家里的内景——饭桌、台灯、茶壶,特别是那个金属铸的大柴火炉,它就像一个沉静地坐佛温暖着屋子。它制作精美、有年代感、而且身体还很有力量,正如它的制造商魁北克蒙塔尼在铭牌上宣称的那样出色,而且它让埃文斯待在那的大部分时间都有事可忙。丽芙和弗兰克都觉得看着埃文斯捣鼓相机拍照的经历很难忘。就像弗兰克回忆时说的:“沃克来造访我们,这就是他全部想做的事了。很多天他都待在那儿,看着炉子,等着火光亮起。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埃文斯拍摄弗兰克家中经典的炉子的照片,同时也让他想起了1936年,他在阿拉巴马州佃户农民家中的书房里,拍摄的壁炉、壁炉架、火炉、床架。那组照片发表在《现在让我们来赞美名人吧》(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还有他和弗兰克在1955年在《财富》一起发表的那一系列手工工具的照片。火炉的照片也向弗兰克自己的作品《美国人》致敬,特别是他对从纽约到内华达酒吧里闪闪发光的自动点唱机的研究。
除此之外,火炉还照亮了弗兰克阴暗的屋子,火炉好似反射了周围海水透明银白色的光,向这个落座在地球边缘的,不怎么有生气的屋子带来了一束安静清幽的光。
在对埃文斯造访新斯科舍省的感想里,弗兰克表达了看着老朋友摆弄相机时诚挚的喜悦之情,同时他似乎也发现埃文斯拍摄的柴火炉的照片是值得被看成一件艺术品来思考的。弗兰克在纽约的布利克街工作室里没珍藏多少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但在墙上就钉着一副埃文斯的马布柴火炉的照片。
《Looking in: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英文名Looking In: Robert Franks The Americans )是一本展示、解析弗兰克《美国人》摄影著作的摄影画册,由于其资料的丰富和详实,使其成为研究《美国人》的珍贵资料。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美国人》几个版本的不同,以及弗兰克的书信和手稿材料等。附录中,包括了底片展示等珍贵资料,资料的完备和详实使其成为《美国人》的权威信息来源。
我们将在未来组织志愿者对该书进行翻译,热忱欢迎各位朋友鼎力相助。有意参与翻译工作的朋友请联系微信号:antphotos